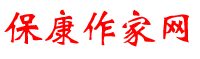大荆山笔记
时间:2019-05-09 点击: 次 发布者:佚名 - 小 + 大
大荆山笔记彭宗卫 我看山水修平老师嘱咐写一写家乡的旅游文章,我欣然应命。在键盘上停留很久,却不知从何处下手。头勾在裆里想了半晌,突然发现,我似乎对荆山南北的旅游有了新的发现。 两河夹一山,便是保康。大荆山横亘保康,将三千多平方公里的江山一分为二,历来是地分南北,人分南北,口音分南北,风物也分南北。沮水、南河一南一北,均衡滋养。南河投奔汉水,沮水汇入长江,寻找各自的功德荣耀。南河势大,两岸土地贫瘠,山势陡峭,人多现实。沮水柔和,两岸土地肥沃,山地平坦,人群处世多讲仁义。我没有褒贬之意,只是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不能不沾这水性、土性,或善或恶,或美或丑,都是苍天厚之意。 在我心中,保康的旅游既不在一个山寨土包,也不在一个痴迷泉眼,更不在某一个沟峡之间,而是一个风物长廊,一个景观宽带。荆山其实是一条旅游走廊,沮水其实是一个景观宽带,不可拆分为一条沟,一个峡,一眼泉,一座岭,肢解的荆山失去了真实的美,局部的沮水不足以打动人。我不知保康山水在旅游管理者心中是如何规划,又是怎样一个盘子收藏在他们心中,但我看来,这规划盘子是零碎的,缺少俯瞰之势,整体之感。 史志典籍中多处提及荆山、景山,其方位均在关山。依山脉,关山为荆山主峰,它在歇马镇境内。如今的歇马镇有5万多人口,面积占保康全县版土面积的六分之一,辖1个居委会、49个村委会。有人把《黑暗传》称作“汉民族的史诗”,而歇马却是《黑暗传》真正的故乡。在歇马的村庄里,多处有民间艺人曾经传唱过《黑暗传》,还保存着手抄本。在我熟悉的老艺人陈长维手上,就有四个《黑暗传》的抄本。 深山藏古风,只是很多人不知风从何处来。如果说歇马是史诗《黑暗传》的故乡,那马良却是沮水巫音的流传地。至今,马良还保存着一百多个最原始的巫音曲目。一个喇叭,一个战鼓,一个边鼓,艺人在表演沮水巫音的时候,常常展示偷换气、换拇眼和抛马锣等特技,烘托现场的热闹气氛。 一个《黑暗传》,一个沮水巫音,沮水边上相隔不到二十公里的两个乡镇,2008年同时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十分罕见。这也是保康旅游的文化软实力,值得深挖推崇。 两河夹一山,这河是怎样的河,山又是怎样的山;山怎样孕育了河,河又怎样显衬了山;山上住了什么样的人,河里流走了什么样的光阴——一路路盘问下来,我笔下的文章就有了眉目。也罢,尽我所能,写我所行,记我所想吧。 走油山出三峡,望荆门,用一双大眼望过去,有一脉巨峰逶迤而来,把江汉平原倚定,这便是大荆山。沮漳二水出得荆山去,抱着千里沃土,追随着长江,养育了几千年的荆楚。 人类总爱寻找自己童年的影子,就像孤独的孩子迷恋地寻找自己的母亲。出于这样的动机,杏黄麦熟之际,一帮朋友相约,从沮水的下游出发,沿着大荆山去寻找沮水的源头。 车沿着保宜公路西进,这是我非常熟悉的行程。我无数次想象到,在中国地形图的沙盘上,有一个巨大的弧形凹谷地带,西进神农架,东出宜昌——每次从宜昌回故乡,我都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又一次沿着这个巨大的凹谷波折线,盘旋而上。蜿蜒西进,出螺祖故里,过三国旧址,进入古镇歇马,径直往神农架方向奔去。 我曾经走过金沙天险,也走过乌蒙滂沱,那一路的沉思像一园累累的果实,挂在我的心田。此时,我走进故乡大荆山的怀抱,迎面而来,有了母亲怀抱的体温与暖香,直教人有些晕醉。只是不知道,我的沮水会以什么样子承等我? 沮水的源头在哪里?《淮南子》载:沮出荆山。另有史料载: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淮水,东南过临沮县界,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举,峻棘层云。 对很多人来说,史书上的记载只是一个陌生的字符。2013年春的一场新雨过后,层层新绿上浮起仙境般的迷雾,云雾让人对大荆山产生种种猜测。回故乡找沮水源头的路上,我总在想,史书上载有“虽群峰竞举,而荆山独秀”的字样,虽然我从小在大荆山里长大,却不知沮水的源头在哪里,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形容我此时的尴尬心境再合适不过了。 保康地处长江三峡、武当山、神农架三个名胜对角线交叉地带,建县时间并不长。就山势而言,保康“东枕岮峪,南带峡沙,西控笔架,北接乌垭,屹然岩险之隅”。多年来,大荆山就像一幅巨画,挂在我家门口。推门,见荆山云兴霞蔚,日起日落;入山,在荆山上打柴挖药,讨吃讨喝。大荆山是我生命中的山,是我命运中的景仰。 五百年前,郧阳府房县的边远山区,人们称之为“川陕楚老林地带”。这里土地空旷,烟村稀疏,成为四川、陕西、河南、江西、山东、山西各地流民逃荒避难之所。流民们挽草为记,搭棚而居,守着荒山老林中的处女地,采掘以食,垦荒度日。由于生活太艰难,流民和当地土著结伙同心,抗捐抗粮,揭竿起义。官府警觉,于是张贴禁令,不准流民进山,大肆捕杀违令者。明朝政府弘治十一年(1498年4月),朝廷见禁山的措施未能挡住流民涌入人山区,加上房县辖境辽阔,地方官鞭长莫及,难以施治。于是,朝廷降旨对这些流民编户抚治,附藉耕种,强制纳粮,强制当差,并辟出房县东部的宜阳(保南)、修文(保北)二里,割地分置,设保康县。这便是保康县的由来。 我在歇马生活了二十年,熟悉歇马境内的大多数山川河流与人文风情。想那五百年人间万象,不过弹指一笑而已。沧海桑田,时移世改,我的目光和想像已经无法穿越。近百年来,砍伐、烧炭、开荒、耕种、修路等过度开发,山变水变,让我的想象再也无法穿越历史回到史书记载的沮水旁边。 歇马境内有多处龙潭,按照志书记载和民间口传,沮水源送的这个“龙潭”应该在歇马镇的欧店。欧店境内,野生蜡梅、野生牡丹、古桩紫薇、云锦杜鹃等野花资源极为丰富。志书记载,“保康南百二十里有一个龙潭,地名歇马河,岩高千仞,半坡突开一洞,水声潺湲夹石间而出,乃歇马河源。”如今的歇马,是保康县的人口和资源大镇,原来三个乡镇合并,人口近五万。欧店在歇马镇西南角,从歇马西去不过一二十里路。 《山海经》载: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沮水出焉,东南流于江。——这景山就是大荆山的主峰,现在叫关山,在保康县欧店镇千家坪村,海拔二千米,是整个襄阳境内最高的山峰。油山村在关山脚下,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不便利,全村二百多户千余人。油山村是歇马镇人口最少、分布最分散、交通条件最恶劣的村,村民出山,要走九公里崎岖的确山路,沿途要绕过二十四条弯弯曲曲的溪沟,若遇雨雪天气,交通完全中断,油山村便与外界隔绝,村民们深受其苦。2008年,油山村避开河道,利用原有地势,沿山爆破,半山腰凿路,工人风餐露宿,村民主动给筑路工人做饭送饭,用时近七个月,建成保康县投入最多、难度最大的一条村级公路。有了这条路,我们便可以驱车直上,进油山村,访沮水源。 我佛慈悲,让我选择在这样一个暮春时节去访沮水源。车逆水而上行,从欧店街左转,我们沿着响林沟盘旋上山。路的尽头,我们弃车步行三四里,抵达沮水的源头——一个叫龙洞的泉水边。村人告诉我们,沮水的源头其实有两个龙洞。一个在油山坪的左边,一个在油山坪的中间,水桶大的一股清泉冒出来,漫过石窟,浸过路面,落下山坡,冲下深谷里去。于是,它有了名字,叫响林沟。一行人这才明白,起初,沮水只是一条沟,后来汇成一条小溪,再后来才叫一条河,最后它有了名字,叫沮水,出山去。 抬头望油山,那一瞬间,油山把我浮躁的心给征服了。隔着一个世纪的爱恋,我们同时喜欢上那一面向阳山坡——每一座山都那么安静、庄严、温顺,每一棵树都舒展着自在快乐。在油山的怀抱里,是一排农家土屋和宽广的田地。惊鸿一瞥,这一片亲近的山水,比乱世中坚贞不渝的爱情更加迷人。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曾经在无数个暗夜里随救护车奔走在荆山下的沮水两岸,过有长达十几年的劳累和伤感的日子。她十分感激大荆山里起伏的群山抚慰自己,怀念沮水边熟悉的树林。在那些黑暗的长夜里,她曾经无数次含泪看着山,看着树,随着体力上的累,心里对消逝的生命产生浓浓的悲凉和忧伤。看着山,看着树,慢慢的眼泪就风干了。 有一个同乡朋友,我们一同在荆山沮水边长大,后来远离故乡去广东教书多年。有一回,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讲到“少小离家老大回”,讲着讲着,想到沮水,眼泪不知不觉淌出来。话音停下来,课堂上,孩子们莫名其妙地望着老师。 千年万年,沮水从我家门前流过。我在沮水边长大,在沮水里泡了十九年。沮水,是我个人的精神长河;荆山,是我内心的精神圣山。长大后,我逃离荆山沮水,一个人在外被爱、被伤害,读人阅己,在谎言的世俗里日渐消磨青春时光。但我每年都要回去看望故乡的沮水,在沮水边洗衣濯足,在大荆山里帮母亲种地。我的沮水荆山,在远离你们的日子里,不论是竞日的舟车颠簸,还是无聊的行旅蜗居,我都在心里默默叨念你们,想象你们妩媚的样子,度过这些庸常难挨的日子。 三十年多年来,我用我的笔,不停地写下对一座山、一条河的怀念,这些文字是我对沮水荆山的承诺,也是我内心最遥远、最高傲的飞翔。 沮水恋沮水河是一条很旧很老的河,现在连一条小小的舟子也没有了,可是很久以前有。 沮水河是从神农坡里下来的,源头在哪里呢,没有地理学家来考评,方志办的人就依据老书上的一行文字,往高高的山里一指,说发源在荆山里吧。站在歇马镇上四顾望去,一脉一脉都是绵绵的山,围住中间一个不大不小的盆地。沮水从盆地口上流下来,响林沟、衙门沟、龙王沟、堰坪沟、庙沟、石板沟、柞溪沟、响潭河共八条水系在歇马这地界柔柔的汇齐了,一路抱着山弯,清清凉凉地下马良镇去。这条河水育得两岸满畈好田,谷丰米香,养出一位位多情细腰的女子,出得荆山去,把脉气扩展得很大哩。歇马镇便享誉在外,外地人嘴巴一溜,便说出这样的话来:“欧店的狗子,歇马的女子,马良的痞子。” 乡里人更是津津乐道此事,哪管什么阳春白雪。盘了田地里的活路,男女老幼的没了伤心和烦恼事情,再穷再苦的地方,白天黑夜的辰光是一点不会少的,一样一样地要把风干的日子打发走。山上人赶牛下河,犁地换钱,纳凉吃烟或喂嘴下棋时,就给东家说,夜里的声音弄那么响,男女东家就吃吃地笑一回,说:“你在床底下喝了云雾茶的?”众人哈哈连天,快笑一回。老辈人聚在一起,有的说日子这样快,眼一眨就又换了一茬人了,人老起来这样快,简直不经活。有的说,屋角的树长得这样慢,看着胡子一天天地白了,等着它做寿屋腌肉呢。也有的说,东街吴家的女婿官做得越来越大了,都以地区当头头儿去了,过年开个小车子回来,威风得像他妈啥子,不得了。众人心气平和,只是感叹日子短了些,还是短了些。 背鸡蛋、羊腿、火纸和兽皮的山上人从官道下边上来,挑盐的、吹响器的也从下边上来,过歇马镇下边的一个村子,有覃寡妇会从屋子里撞出来,拦住混身是臭汗的山上赶脚客,把憨巴的山上赶脚客说得服服帖帖,心甘情愿地把东西卖给她。覃寡妇的铺子于是有就了些头脸,请人把店门的板壁做得宽大厚实。传说她年轻时开“美国饭店”,是上下河里风流得要死的人物。乡里城里又没有专门管睡觉的警察,寡妇也是乡里民间的一种文化,她跟任何男人睡觉,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歇马见怪不怪。大家想,没有男人管的女人也许活得更快活些。 早些年沮水河里发大水,淹死了不少吃水上饭的汉子。两岸青白的卵石,衬着晃晃桥上的人影,悠啊,摇啊,真的就觉得沮水河是一条很旧很老的河了。 我的家就在歇马镇下边的村子里,叫烟墩,村子里家家吃沮水过活。村子像一贴膏药,贴在歇马镇这个大盆地的中心。村头的渡口已经消失得快要认不出来了,只是从老辈人的记忆里还依稀感觉到:呵,渡口!跑大船呢,活蹦乱跳的男人都顺着河水出山,到长江里去吃大饭去了。每当落日挂在沮水上方,就仿佛天地无限遥远,这使得歇马镇看起来很美丽,空旷无边。 这都是很久前的一幕了。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谈说这些。我因为太爱沮水,曾把初恋留在它的身边,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 祖父背盐我是一个背夫的后代。七十年前,我祖父是一个鄂西北深山中一个背盐的民夫。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我祖父的命运注定与沮水荆山相伴。沮水出保康,已经是一条巨流河,它擦着南漳县的边界流入远安,沮水流经远安的洋坪、旧县、鸣凤、花林寺四个乡镇。它由洋坪镇南襄城入境,至花林寺镇,从雷打岩出远安境。这个洋坪旧镇,昔日号称“小汉口”,是鄂西北有名的水陆小码头。旧时的保康,因为交通十分不便,商业凋零,更谈不上繁荣,商品流通上,北边顺南河去向老河口,南边走沮水下远安的洋坪。 年轻一代的保康人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祖父辈还有“背夫”这种职业。在我祖父那一辈,他们心中的向往,就是走出大荆山,下洋坪,跑宜昌,到沙市,把山货卖了,换回生活用品。我的祖父就是鄂西北荆山古盐道上的背夫,他的足迹曾经踏遍荆山沮水,在年轻的岁月里,把血汗留在了出保康、下远安的古盐道上。 川盐进入楚地,历史上著名的事件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川盐从长江三峡出川,在宜昌和岳阳上岸,分销到湖北、湖南各地,像一条灌溉的沟渠,到宜昌这里,被分配到千亩万亩良田绿地里去,流进千家万户。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据宜昌,川盐出不了西陵峡,只好从三斗坪上岸,由挑夫背夫们用肩膀驮了,翻越崇山峻岭,运进汉江平原和三湘大地。另一条通道是从川东到鄂西恩施,穿越十万大山,入神农架,经大九湖古盐道,进入房县和保康境内。 兵荒马乱的年月,在鄂西北十万甚至百万背盐大军中,有一个卑微的人物,个子瘦削矮小,青布衫子,白棉布袜子,草鞋裹脚,他便是我的祖父——一个十四岁就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的男人。 有关祖父下洋坪挑盐的故事,祖母翻来覆去讲给我听,我前后听了三十多年。四十多年后,当我行走在中国盐都——四川自贡的街巷,静静地望着自贡盐业博物馆深宅大院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祖父当年在鄂西山道上双肩背盐蹒跚而行的身影。那时候保南下宜昌,没有宽阔的车马道,只有翻山爬岭的人行便道,走男走女,行兵过匪,是这山道的使命。 远安县洋坪镇处在南漳、保康、远安三县交界之地,舟楫往来便利,既然叫“小汉口”,便如同私生子像真老子,自然就有老汉口的味道。洋坪的货铺、客栈、饭馆、酒铺、茶馆、花行、布行、盐行鳞次栉比。荆襄人善长做手工活,织纱幅子,做凉帽,绣花鞋,商贩拿这些东西到洋坪来,换山里的山珍土产,茶叶、药材、火纸、羊腿、竹麻、木器,换一家人的柴米油盐。保康大山里物产丰富,出产生漆猪毛、木耳香菇、名贵药材和兽皮麝香,商贩雇挑夫挑出山,在洋坪街上卖了,换成布匹盐巴,挑回山里去,在歇马街上卖了,天长日久,买卖就一天天做得很大。 背盐是枯燥的,血汗流尽,打不动看客的心。不谈背盐路上的艰辛酸苦,也不谈土匪如何劫道取投名状,倒是祖母常在嘴边上讲起的笑话,引起我对祖父无限的想象。祖母说,祖父是一个风流祖父。“大年三十晚上,还有女人赶着给他做鞋子,正月初一早上送到他脚上。”说完,祖母打一串哈哈哈,无比的宽容。我不知,这一点野性的温情来自何方,但我理解,这也许是祖父寂寞的背夫路上难得的梦乡吧。 以祖父的人格判定,她断然不会是洋坪镇上的一个婊子。婊子没有这样的情义,不会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还赶着给祖父做新布鞋穿。婊子没有这样的温柔,不会让我的祖父长久地迷恋她。背夫靠的是脚力,她心疼祖父的那双终年散发着汗臭的大脚,这便是一个女人的魅力,是一个男人的傲气所在。作为一个男人,祖父把家扛在肩上,绑在脚上,拴在身上,他十几岁开始背盐。后来攒下钱,买了一头驴,再有了二头驴,他有了小小的驴队。随着祖父小小的驴队出现在鄂西北深山中,我想象有一个漂亮的少妇,把目光投向我的祖父——那时候,他还不是我的祖父,他是一个年轻的丈夫,一个全身都是力气的男人——我祖父把这样一个女人揽在怀里,表现出所有歇马男人都有的温柔情怀,在歇马至洋坪的古道上,留下了一段或长或短的风流岁月。 假如,我祖父没有这样一个大眼睛的女人,那么他的故事是不完整的,他的人生将会呆板得多。他不会那么长时间地奔走在这条毫无生机的羊肠小道上,他不会那么兴趣盎然地发展他的驴队,他不会在夹缝岁月里积攒下八块洋钱。我的祖父是响当当的祖父,他的六个姐妹都嫁给了地方,他自己宁愿做一个背夫,出山、进山,歇马、洋坪,在这段距离上丈量思考自己的生命与现实。除了我的祖母,我确信还有那么一个女人在等着他,他们有约定,有期待,有鼓励。生活的大门向一个背夫打开了一条缝,他登堂入室,静悄悄地投向了那个命中跟他有约的怀抱,践一个男人的约定。 假如,那个大眼睛的女人没有遇上我祖父,那么她的生命将会暗淡无光,任凭沮水把她的身影流走,也许会有另外一些粗野的大手把她掠走。不知是几世积下的缘份,让她在洋坪遇上了这个赶着驴队的男人。他是前去投店,还是找地方饮酒?抑或只是上门找一口水喝,他认识了大眼睛的女人。她也许是一个赶场的村妇,也许是一个丧夫的寡妇,也许是一个过门不久的少妇,也许只是一个走路扭了脚的路人,被我的祖父伸手扶起,就在某一个瞬间,接通了生命的电流。我祖父在背负盐巴山货的同时,也背负了一个女人的嘱托,背上了大眼睛女人的目光。——我体谅到祖父作为一个男人的劳累,从身体到内心,他都肩负着重量。 假如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女人出现,我祖父可能会抽大烟,可能会赌洋钱,可能会玩花牌,守着几亩薄地过一个佃农的小日子。动荡的时代不是他的,战乱的年月不是他的,往来的财富也不是他的。毕竟生活不是假如,人人都朝着上帝给自己安排的命运而去,不偏不倚,各行其道。祖父的故事就这样发生着,他赶着驴队,在下洋坪的路上挣下了八块洋钱。 民国三十五年,一场瘟疫,家里死了八头猪,四头驴。故事在这里发生急转,失去驴队,就像战士被缴了枪,祖父被迫留守家乡。歇马镇上传来阵阵枪响。匪事冲淡了情事,现实打垮了温情——祖父不能再下洋坪,他开始守着几亩薄地过日子。三年后,在歇马镇解放前夕,他把自己辛苦挣来的八块洋钱埋在老屋旁边的牛圈门口。 八个银元,这一埋就再无用场,再没有人想起。1975年,祖父病逝。世事阻隔,家中变迁,直到1981年,镇电管站雇民工挖坑埋电线杆的时候,才在牛圈门口挖出了八块洋钱。物是人非,野地里埋了三十多年,被一群无知的人偶然挖起来,没有人证物证,银元自然是谁挖到归谁。父亲只是走上前去远远的看了一眼。 祖父去世那年,我六岁。在我的记忆里,祖父长得面黑须少,身不高、腰不阔,常年黑帕缠头,上穿深蓝色粗布褂,下穿大裆灰裤,白布长袜裹腿,脚下穿一双手工做的草鞋。这是祖父在1975年生前留给我的印象,我写此文时,距离祖父下洋坪挑盐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 圣经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如果失去了味道,还能用什么来把它腌成咸的呢?它再也没有用处,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细细想来,祖父和我们,以及我们未来的儿孙,都是地上的盐。我不想失去咸味,只想躲进岩石缝里,做一朵石头上的晶体泪花,自枯自荣。
|
上一篇:灯影婆娑山城夜
下一篇:朝元山记
- 06/28保康县历届主席团成员
- 04/282020紫荊花诗歌奖·“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
- 06/13姜雪琳
- 05/02文化保康建党百年大事记补
- 05/05李修平
- 07/01秦雨
- 05/12王明瑞
- 05/10高明英
- 07/10保康县第六届主席团成员
- 03/10“用爱征服,用心铭记: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
- 07/24避暑神农架
- 07/24在2021年度襄阳市作家协会年会暨“光华特杯..
- 05/26保康县作协开展“到人民中去”文学志愿服务..
- 05/25只留清气满乾坤
- 05/25只留清气满乾坤
- 05/01高昌英
- 05/01汪递强
- 05/01杨丽
- 05/01张咏
- 05/01李敬相
- 01/052022年保康作协工作总结
- 07/24在襄阳市作家协会 2021年会上的 致 辞
- 07/24文学盛会聚保康 山林支队获殊荣
- 05/26保康县作协开展“到人民中去”文学志愿服务..
- 04/20保康县作家协会2022工作会议召开
- 04/20抒写“红色黄堡,绿色乡村”笔会成功举办
- 12/27凝心聚力 为文学事业修路建桥 ——2021年保..
- 11/18保康县作家协会举行 学习六中全会精神、激..
- 11/01保康作协“助力惠游湖北·奉献文化情怀” ..
- 06/08李修平考察尧治河文学创作基地
保康作家网 bkzj.xysww.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保康县政府大院12号楼61327信箱
联系电话:13597488059 13908677897
投稿信箱:2052739087@qq.com 522456581@qq.com
法律顾问: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