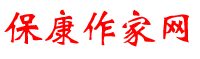我最牵挂的那个人走了
时间:2020-05-01 点击: 次 发布者:佚名 - 小 + 大
“我今儿到我妈那儿吃饭。” “放假回家看我妈……” 每每听同事们说这样的话,我总会咽下已不能和她们一样叫妈的悲凉。有妈幸福,天天把妈挂在嘴边,真好。 2013年阴历11月14日晚上,我打电话回家问妈身体。三哥说,13日清晨,妈左手和左腿突然麻木了,自己不能穿衣服了。挂断电话,我的腿一下子软了。当天上午,我们匆忙驱车回家。本打算把妈送到县医院检查治病的,谁知妈晕车厉害,一路呕吐不止,只好就近送到镇上医院治病。 经检查,妈属于轻微高血压中风偏瘫。经过医治,妈从最初说话含糊不清,左手不能端碗吃饭,到后来基本都能自理。妈出院后,住在弟弟新盖的房子养病。那年妈已83岁。 妈住弟弟家养病期间,弟弟、弟媳照顾无微不至,可妈一直住不习惯。打从住进弟弟家,她没有一天不念叨要回老家的。每次回去看她,见到我就愁眉苦脸,还重三遍四跟我说,要回去,要回去。还说不能死在弟弟家。任你怎么劝,她也听不进去。 2014年夏天,妈的大脑突然失去了记忆。我去弟弟家看她,剥香蕉给她吃,她突然问我香蕉是咋做的?还仰起头,愣愣地看我半天,认不得我了。一会叫我姐姐,一会又把我当成老家邻居梅子。我心想,若是妈出院后,就顺从她,然后姊妹们轮换照顾,她一定很开心。可是我们姊妹都忽略了妈的感受,这样孝敬,反倒是害了妈。 没过几天,妈再次病重住进医院。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不吃不喝不睡觉,整日整夜胡言乱语。身体枯瘦如柴,全靠打点滴维持生命。在医院照顾妈,心里五味杂陈。为得到更好的治疗,弟弟又把妈从镇上医院转到县医院。经检查,妈患小脑萎缩,发展到老年痴呆,让我心疼不已。 端午节那天,四嫂遭遇车祸,从市医院转省医院,又转回县医院住进重病室。那段时间,我、我姐、二嫂、还有弟媳,轮流照顾四嫂和妈,个个累得筋疲力竭。而我心情更加沉重。一边是年轻的四嫂,一边是年老多病、会随时离我而去的妈妈,她们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我要把精力和时间分两半。本来体质虚弱的我,照顾四嫂熬夜,照顾妈同样熬夜,还有自己小家庭和工作。那段日子,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 妈失去了记忆,唯一没有忘记的是回老家。在县医院治病,一直吵闹要回去,不配合打针,不吃饭不瞌睡,勉强住了一星期,我们就送她回老家。而在老家,能照顾妈吃喝拉撒睡的只有二嫂。二嫂贤惠善良,对妈照顾细心周到。妈回家那年,侄儿请老中医给他奶奶弄了几副中药。妈在老家一边打针,一边吃中药调理。也是妈福大命大,两个月后,她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转。能吃饭了,家里苞谷收割,还能帮家里搭把手了。只是我们姊姊回家,她依然不认识。我想,不管妈称呼我啥,只要她能健康长寿,回家能见到她,能站在她面前痛痛快快地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就心满意足了。 在二嫂的精心照料下,妈还能拄拐棍到处走着玩了。可过了几天,她硬是不到二嫂家里住了,她说这里不是她的家。二嫂做的饭,她也不吃,每次哄半天,她才肯吃一点。有几回我回家,她贴着我耳根,眼睛瞅着正在烤火的二哥,悄悄对我说:“姐姐,我跟你说个事,那个“老头子”好厉害,他喜欢吵我。”我笑着说:“妈,他是你的儿子,我的二哥啊。他是怕你听不见,说话声音大了点,不是吵你呀。”妈争得脸红脖子粗,举起拐棍把墙壁和门框敲得嘣嘣响。 老屋就在二哥的门坎下面,距离二哥家也就200米远。2015年春上,为照顾妈的情绪,二嫂二哥只好将就她。让她回老屋住了。 老屋是妈和爹从年轻时一起打拼的家,妈一辈子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浓缩在老屋里。自爹2005年去世,妈便和未成家的三哥相依为命,一直住老屋。三哥出门干活,妈在家做好饭菜等三哥回家。那时妈已76岁了,她依然把菜地和家务打理得井然有序。自她病倒,再不能做家务了,三哥只顾忙农田活,连饭都不能按时吃。家里便有些凌乱不堪。可是妈病了还是要选择跟着他,真是苦命。 每次回家看妈,我好想一心一意陪着妈。多为妈做点什么。可是我看到三哥换下的衣服要洗,地里的菜也要割回家腌制,堂屋里堆成山的苞谷棒子也要剥,地面脏了也要打扫,总之有忙不完的活儿。这时,心里便沉甸甸的,乱糟糟的,像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好一面照顾妈,一面做家务。可是在我做家务的时候,妈没人陪了,无论外面大晴天还是刮风下雨,她说出去就拄着拐棍出门了。从三哥门前场子绕到屋后二哥门前的场子,甚至走得更远。一边走一边胡言乱语:“唉哟,唉哟,我心里没得法啊,我咋不快点死啊,死了才好,活到有啥用啊。”妈歇斯底里,大声诅咒自己赶紧死掉。妈因身体难受而疯狂,而她的疯狂又像一根根扎在我心头的针。老天爷好像要把积蓄了几十年的磨难,一股脑全部灌进妈娇弱的身体里,她就像狂风暴雨中一株小小的草,被千钧重的冷水打湿,打瘪,直到碎进泥里,碎进我心里。 我生怕妈摔跤,心里揪成一团,赶紧放下活儿,把妈从外面找回来。牵着妈的手,哄到火笼屋烤火,找零食吃。再三劝嘱:“妈,外面好冷,你坐火笼屋烤火,出门怕摔跤啊。”她边吃零食边连连点头。可是我刚转身,她又悄悄拄拐棍悄悄出门了。 妈回老屋住了,衣服虽由二嫂洗,三餐由三哥做了吃,晚上起夜由大哥照顾,可我还是牵挂她。我白天想的是她,夜里梦见的还是她。要是他们都忙了,妈每天会不会按时吃饭吃药?天冷了会不会及时添衣裳?鞋子自己穿反了,衣服没穿板正,他们会不会及时发现?出门玩,腿脚不灵便,会不会摔跤?一想起这些,我心乱如麻。 2015年“十一”放假,我本打算回家看妈,结果在放假前天晚上,外地有个亲戚到保康,让我们带她们到景区玩,到了景点,我接到二嫂电话。她说妈一个人拄着拐棍走到屋后垭子口了,连哄带劝才把妈哄回家。二嫂上说妈吵着要到我们姊妹家里玩。妈有记忆了,我要接妈到家里玩,晚上把妈的双脚泡得热乎乎的,抱着妈的双脚入睡,白天陪妈逛公园晒太阳,给妈做好吃的……那晚我总是想着再和妈相处的小小幸福,激动得通宵未眠。 第二天清晨,我匆忙赶到马良镇,和弟弟一起回家接妈。一路心情愉快,看啥都好看。可是妈到弟弟家那晚上,又犯病了,不吃饭不睡觉。拄着拐棍在屋里走来走去,还老吵嚷着要回家。我跟在她身后走累了,可她就是不坐下。那晚上姐夫也在弟弟家吃饭,我指着姐夫,一本正经对妈说:“妈,你看那个人就是医生,你这样子大吵大闹,医生可不喜欢。”妈瞄了一眼姐夫,小声对我说:“好好,我不吵了,等吃完饭了你送我回去。”那次勉强哄妈在弟弟家玩了3天。就送她回老家了,从此,妈再不能出门了。 2016年夏天,女儿放署假,我带女儿回家看妈。一进门,见妈拄着拐棍在屋里站着,见我回来,她走近跟我说:姐姐,我屁股好疼,坐椅子疼得不得了。”说着双手扒下裤子让我看。不看不知道,一看惊呆了。发现妈原来长过囊肿的位置,旁边又长了个囊肿,已有小碗口那么大。唉,三哥只顾忙活,忘了还有个妈。我急忙打电话联系村卫生室医生。医生到家,用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才把囊肿给处理掉。妈很坚强,我看见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她没吭一声。 2016年12月,我再次打电话回家,三哥说妈感冒了。我赶忙请休假,买药匆忙赶回家。那是我与妈相处时间最长一回,也是最后一回。 回家第二天,天气睛朗,没有一丝风,一丝云彩,心情像蓝天一样爽朗。吃罢早饭,见妈又拄着拐棍准备出门,我担心妈会摔跤,用篮子捡来苞谷。和妈坐在门前场子边晒太阳,掰苞谷。这时候,三五成群的鸡仔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一点都不害怕。妈边掰苞谷,边微笑着看身边的鸡仔,不时低头抓一把掰好的苞谷籽喂鸡仔,还自言自语:“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好啊。”感觉妈白天精神挺好,也不咳嗽,可一晚上就咳嗽不止,且越来越严重。 12月8日清晨,我给三哥商量,趁我在家请医生给妈打点滴。下午四点多,医生才挎着药箱,骑着摩托车到家。妈高血压中风,又脑萎缩,大脑多半糊涂,打针不能离人。我坐在妈身边握住她打针的手,寸步不离。 那天,二哥与我聊起家乡的人和事。妈耳朵尖,二哥说话时,她要么嗒嗒腔,要么微笑望着我们。晚上8点多,吊针打完了。我给妈炖了个鸡蛋,让她自己喂。估计是打针时间长的原因,妈的右手突然不灵活了,用勺子喂鸡蛋,一半洒在衣服上。我忙接过碗喂她吃。妈吃完蒸鸡蛋说还想吃。我心想,妈能吃饭了,说明药见效了。可吃饭不久,妈突然歪下身子,躺在我膝盖上,双手死死抓住我的手不放。我吓得一声连一声地喊她。可妈就是不说话,双眼紧闭。 约摸10分钟后,妈慢慢抬起头,我问她:“你刚才咋的。哪里不舒服?”妈眼里噙着泪水,望着我说:“我看见我的爹和妈了,爹在门前田里耕地,我在后面丢苞谷籽……妈这一说,我心里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 那天晚上,是妈最难熬的日子,也是我最忘不了的日子。她想睡觉,可是上床,还不到10分钟就要起床小便,起床后又尿不出来。再次躺下,再次穿衣服爬起来,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被单尿湿了,穿的内衣裤全都尿湿了。我从箱子翻出被单垫床上。刚让她躺好,她又喊着要起床烤火,还说怕睡过去了。家里夜晚特别冷,三哥熬夜撕苞谷深夜才睡,我又不忍心喊他起床生火。我硬是哄妈躺在床上被病魔折磨到天亮。妈睡在床上那么难受,我却没有顺从她,我愧对妈。 妈能走路,卧室又在二楼,再跟三哥住老屋,实在不方便。二嫂主动把妈接到自己家。妈住二嫂家,一日三餐能按时吃,她家的火笼屋比三哥家里热乎,我心里踏实些了。妈再不能自己走路了,精神倍减,不再像往常那样,嘴里念叨不消停的是大哥二哥三哥的名字。家里来客人了,不再打破沙锅问到底,这是哪个?那个又是哪个呀?而是低着头,眯着眼,双手总是想伸出去找东西揪。不是扯衣服袖子,就是把衣袖某一块用两个手指头拧起来,使劲儿揪拽。手里拿的擦脸纸巾和毛巾,老是往嘴里塞,我可怜的妈,她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离开二哥家时,妈再也站不起来送我了,也不喊我姐姐了。她低头不语,双手要么不停地揪衣服袖子,要么就是坐椅子上打盹。我把妈正在揪衣服的双手放到手心,摸了又摸,强忍泪水说:“妈,我回去上班了,等放元旦假再回来看你啊。”不知妈是否听到。当她双手离开我手时,又不停地揪自己的衣服,恨不得把衣服都撕成碎片…… 妈双腿瘫痪,只能坐和睡。坐在椅子上,二嫂要是忙起来,身边没人守着,不放心。我爱人找残联申请了一把轮椅,下午弟弟把轮椅带回老家。轮椅带回家的第二天,我问二嫂,妈坐轮椅是否习惯?二嫂说,妈坐在轮椅上用带子系着,睡觉放心。我知道,伺候妈不是个轻松活,要喂饭喂药,换尿布,晚上还要陪着熬夜,加之二哥肝病多年,不能做事,二嫂一个人够辛苦的。我打算元旦放假再回家照顾妈,让二嫂睡个安稳觉。 2016年阳历12月26日,二哥在电话里跟我说,妈的精神特别差,不知能否熬过年。当天中午,二哥突然来电话,说妈走了。按阳历时间,那天妈刚满87岁,离阴历时间还相差28天。 妈这几年一直病着,我也早预料到这一天,可我还是无法接受,无法接受的是我们姊妹虽多,可是妈在身体硬朗时,她总是体谅三哥一个人过日子艰难,却很少到其它儿女家里玩。 我赶回家,妈已经平躺在床上,脸上盖着火纸,等我和四哥回家给她穿衣入敛。我趴在妈的床边,握着妈余温尚存的手,心如刀绞。我明白,此后,我与妈将阴阳两隔,再回老家,进门再没有妈喊了。 妈走两年多了,我仍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在街上遇见和妈年龄相仿、 身体又很硬朗的大娘, 我会不由自主走上前去,问人家一句:“您老人家高寿啊”?问过了,走过了,还得回头再看上几眼,心里不知问个多少遍:“为什么人家还活得好好的,头脑那么清醒,跟着儿女享福,而我妈怎么就那么走了?每每听到有人叫“妈”,我仍然会驻足片刻,回味着我也能这样叫“妈”的时光。在商店看见适合妈穿的衣服,又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摸,默念,我妈皮肤白皙,穿这个颜色好看。待我回过神来,又会心痛好一阵子。 有一次,梦里我又回到老家了。一进火笼屋,脚刚跨进门坎,看见妈在厨房靠灶台边站着,双手抱一起,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短外卦,留着短发,头发幽黑,皮肤白皙,且没有一点皱纹,感觉妈好年轻。妈见我回来了,她笑盈盈地向我走来……梦里,我很久没有回家了,那一刻,我激动得大声喊:“妈啊,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我好想你啊。”说着便跑过去一头扑进妈怀里哭了,哭醒了。 妈在,家就在,爱是完整的,心是丰满的。老家是我安魂入梦的地方,可是现在,爹妈都走了,我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了,心不知往哪儿搁,感觉回家的路离我越来越远。龙应台说过:“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想想,果真如此。 我最牵挂的那个人走了。从此,我只能坐在电脑前,敲打着和妈相处的点点时光,让灵魂得到一丝安宁。 |
上一篇:回家路难离家难
下一篇:万年山上好风光/宋永权
- 06/28保康县历届主席团成员
- 04/282020紫荊花诗歌奖·“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
- 06/13姜雪琳
- 05/02文化保康建党百年大事记补
- 05/05李修平
- 07/01秦雨
- 05/12王明瑞
- 05/10高明英
- 07/10保康县第六届主席团成员
- 03/10“用爱征服,用心铭记: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
- 07/24补理论短板 促文学创作
- 07/24在襄阳市作家协会 2021年会上的 致 辞
- 07/24文学盛会聚保康 山林支队获殊荣
- 05/25只留清气满乾坤
- 05/25只留清气满乾坤
- 05/01陈绪钦
- 05/01陈敬泉
- 05/01马宗佑
- 05/01王承鼎
- 05/01张蕾
- 01/052022年保康作协工作总结
- 07/24在襄阳市作家协会 2021年会上的 致 辞
- 07/24文学盛会聚保康 山林支队获殊荣
- 05/26保康县作协开展“到人民中去”文学志愿服务..
- 04/20保康县作家协会2022工作会议召开
- 04/20抒写“红色黄堡,绿色乡村”笔会成功举办
- 12/27凝心聚力 为文学事业修路建桥 ——2021年保..
- 11/18保康县作家协会举行 学习六中全会精神、激..
- 11/01保康作协“助力惠游湖北·奉献文化情怀” ..
- 06/08李修平考察尧治河文学创作基地
保康作家网 bkzj.xysww.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保康县政府大院12号楼61327信箱
联系电话:13597488059 13908677897
投稿信箱:2052739087@qq.com 522456581@qq.com
法律顾问: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