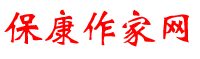山村葛痛
时间:2019-05-04 点击: 次 发布者:褚金鑫 - 小 + 大
褚金鑫 一
关于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楚时期。——“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迫于生存,伟大、智慧的楚先人发明了“捣葛”。后经传承,到了我的父辈这一代,且被发扬光大。贫穷的村民与天斗,与地斗,与山斗,开展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捣葛运动”,村民把这项劳动叫“挖葛根”。他们把毕生的青春年华交付给了葛,宛如他们把期望托付于土地。其实,土地有时也是靠不住的。
偌大一个乡镇,就我们一个村挖葛根。就因为,葛粉救活了村民,救活了村庄。
父亲说,1959年,他七岁的时候,正好赶上饿肚子闹饥荒,村民吃猪草、树皮、老鼠、蛇……凡是可吃之物,都吃尽了。有的吃观音土,全身浮肿,腹大如鼓。由于土不能消化,人竟活活给憋死了。饥不择食,人吃人的也听说过。走在乡道上,看见前方踉踉跄跄地行走着一个老人,脑袋轻轻一耷拉,黄泉路上就又多了一条冤魂。饿殍遍野,哀鸿声声。死一个人,就如死只雀鸟一样稀松平常。希望犹如门前恐怖的群山,一眼望去,没有尽头。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父辈们想起了荆山上特有的救命植物——葛。
葛,属豆科多年生藤本植物,长二三丈,缠绕他物上,花为紫红色。茎可编篮搓绳、晾晒衣物、编织草鞋,称之谓“葛藤”,与村人生活息息相关。根可提治淀粉,有解饥止热功效,提取了葛粉的纤维可织葛布。当地称这种纤维为葛根衣子,是上好的柴禾。村人曾用来填充枕头,后发现枕了这种枕头会引起头疼便不复再用。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村里陈奶奶曾讲述过她生小孩之后把葛根衣子当做卫生纸用。现在想想,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
村庄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挖葛大军。我的曾祖母,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满头银发,提个荆篮,迈着清朝末年的小脚,也颤颤巍巍地行进在这支队伍中,在附近的山坡上拣拾别人遗弃的残根。有时,碰上好心的大叔大伯,也会把采挖的葛根送给可怜的曾祖母一些。后来,采挖的范围越来越远,曾祖母就跟不上步伐了。亦如她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刚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挣扎出来,又掉进了新时期饥荒的深渊。
年迈的曾祖父领着年幼的祖父,永无休止地在山上刨葛根,整个大地被他们刨得遍体鳞伤,宛如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曾祖母和祖母把葛根制成葛粉。来不及剔除泥土及杂质的葛粉称油粉,油粉乌黑浑浊。曾祖母凭着她一双灵巧智慧的双手把这些油粉烙成馍,摊成饼,味道并不比粮食差多少。虽然油粉中有浓浓的土腥味,可作为在大地里刨食的农民,哪一刻没有跟泥土打交道呢?泥土换作另一种方式进入他们的肠胃,入定、涅槃。
村民近乎疯狂的采挖堪比垦荒。山上的葛根越来越少,采挖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跋涉到更远的深山里寻觅。葛根少了,意味着活命的东西就少了,尖锐的矛盾也产生了。村民有时会为了争夺一窝葛根而大打出手,头破血流。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存亡,打架算得了什么?村庄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混战开始了。这是由一窝葛根引发的血案。源于孟二爷找到了一窝葛根,且留作记号,第二天被陈大爷给挖走了。交战的双方是村庄里最大的两个家族,领头的是孟二爷和陈奶奶。孟二爷一家6口,个个年轻力壮。陈奶奶一家10口,除了她和陈大爷、陈大叔能勉强应战外,余下的是一群鼻涕虫与嗷嗷待哺的一对双胞胎。这场战斗,棍棒、镢头都派上了用场,杀戮的欲望搅起尘土,暴怒的嘶吼响彻山谷,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之势。由于实力悬殊分明,最终以陈姓家族失败告终。陈大爷在这场战争中,折了右腿,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 饥饿、疾病、贫穷、灾难让原本脆弱的村庄更加憔悴!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陈奶奶的一对双胞胎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如刚出土的新苗暴晒在烈日中,已然奄奄一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陈奶奶孤身一人摸到了孟二爷家里,委身于孟二爷,只为讨得一瓢葛粉。双胞胎最终存活了。十个月之后,陈奶奶又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即是后来的陈幺叔。村人们说,这陈幺叔与孟二爷怎么会那么惊奇地相像?陈奶奶缄默不语,衰老的面庞沟壑纵横,眼眶中蓄满了昏浊的液体。村人们触及了陈奶奶的隐痛。陈奶奶的隐痛,是整个村庄无法愈合的伤。 靠着这些乌黑的葛粉,父辈们苛延残喘活了过来。
父辈活了。村庄也活了。
二 后来,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父辈们再也不用为肚子发愁了。村人们开始思索如何发家致富,他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葛根。
寒冬腊月,万物凋零,鸟兽敛迹。然而给村庄带来的却是福祉、是憧憬。进九之后,制作的葛粉可长期放置,不酸、不腐。村人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开始了。
鸡子还没叫哩,汉子们就被婆娘从热被窝里赶出来。揉揉布满血丝的双眼,狼吞虎咽吃两碗炒饭。婆娘把泡得浓酽酽的海棠装在一只鳖壶里,摊上俩软饼,装在布袋里,郑重地交给汉子,这可是一天的口粮呐。汉子扛一把镢头,背一把弯刀,点燃一只廉价的香烟,如出征的战士,满怀希冀地出发了。
挖葛根的过程是艰辛的。父辈们钻进海一样深邃的大山里,在荆棘榛莽中不停地奔跑寻觅,如一只迷了路的野兔。两条粗壮的大腿被消磨得如葛藤粗细。方圆几十里的崇山峻岭,哪座山上粉质好,哪片林地土质松,哪条道上有山泉,哪道坡上出野猪……父辈们都谙熟于心,一如自己的身体
夕阳落山,羊肠鸟道上多了一行趔趔趄趄的队伍。沉重的葛根把扁担压弯了,扁担把汉子的身体压弯了,汉子把山路压弯了。他们饥肠辘辘,弓腰驼背,走一步,歇三歇。
回至家里,父亲早已精疲力竭,瘫坐在地上。半晌,才说出话来,狗日的,累得老子血奔心。
时间退回到一个冬天,朔风呼啸,天寒地冻。父亲照常到千架林挖葛根。临近天黑,别人都回家了,唯独不见父亲。母亲心急如焚,你伯莫是遭到了意外?我心里咯噔一下,仿佛突然间掉进了冰窟,心头凉飕飕的。我们去接接你伯吧,母亲说。母亲取来一把竹扫帚,浇些煤油,点燃了。母亲高擎着火把在前,我紧跟在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千架林方向走去。山道崎崛,母亲时不时回头叫我一声,生怕我出了半点闪失。黑夜幽深如井,山道两旁的树木恍如幽灵,冻僵的老鸹出其不意怪叫几声,令人毛骨悚然。走了六七里地的样子,到了西沟口,终于见到了父亲。父亲抱膝坐在一块石板上,衣衫褴褛,葛根散落一地。母亲举了火把,凑近一瞧,父亲的左踝骨肿得像鸡蛋,青紫的皮下积满淤血,腿柱子上撕破的表皮正往外渗出殷红的血珠。原来,父亲挑重了,一天的奔波辛劳,他早已疲惫不堪,加之路滑,走在石板上,两腿打颤,一个踉跄,父亲就栽倒了。看着父亲失魂落魄的模样,我禁不住抽泣起来。父亲鼓着双眼吼道,哭个球?老子又不得死!你给老子好好念书!你将来若不努力,就是我这个下场,一辈子在这穷山沟里挖葛根。母亲把散落的葛根拾掇好,挑在肩上。坎坷的山道上摇曳着我们一家三口弱小的身影。父亲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生活如一条无形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父亲这头超负荷的老牛,牵引着我们整个家庭艰难前行。尽管道路荆棘密布,前途未卜。
葛根采挖回来了。母亲领着我和妹妹刮葛根皮,砸葛根。村庄里此起彼伏的榔槌声如鼓点般密集。父亲俨然是主角,双目圆睁,额头上的青筋暴突,一起一落,干净利落。“砰——砰”,榔槌每响一声,村庄似乎随之一颤。葛根开裂,白浆四溅。我们又凑上前去,将葛根反复捶打至粉碎,放入腰盆、木缸里漂洗,过滤,打捞至模子中挤压,复又捶打,直至榨干每一滴粉汁。榔槌声声,击打着村庄,叩问着岁月。葛根经反复捶打、过滤,沉淀成油粉,再经过反复漂洗,最终形成了白亮亮的葛粉。这个过程叫“整葛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村里,葛粉堪比黄金。整葛粉和挖葛根一样,对人的身体是一种极度的摧残。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刺骨的冷水把父母扭曲变形的双手冻得红肿、粗糙、皲裂,宛如千架林的花栎树皮,褶皱纵横。寒气渗透身体,深入骨髓,如钢刀刮骨,余下的是锥心的疼痛。黑黢黢的葛根水溅在嘴里,又苦又涩,宛如父母的人生。
父母把葛粉团捏成蛋状,放在草木灰中焐干,就是成品了。葛粉蛋提到镇上,即可变现,5角钱一个。买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穷苦百姓,老妪老翁身体抵抗力差,到了冬季,如一只不停拉动的破风箱,葛粉可用来治哮喘、老慢支。孩童头痛脑热,葛粉用来清热祛湿。葛粉蛋若送往县城,身价则能翻一番。买的人都是机关干部,他们说喝葛粉有降低血压、美容养颜、延年益寿之功效。同样的都是葛粉蛋,在不同的人群里卖出了不同的价格。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父亲说。
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背着父亲偷偷冲了一碗葛粉喝。稠稠的、晶莹通透,满嘴清香。我想,要是每天能喝上一碗葛粉,该多幸福啊(虽然我尚不明确幸福的涵义,但应该至少是美好的)。正当我沉浸在美妙的幻想中,父亲冷不丁狠狠掴了我一记耳光。抽得我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地疼,周身不停地颤抖。这是你喝的东西吗?这是一家人的救命钱呐!父亲怒斥道。你不晓得你的学费还没有着落,你妈的药费还欠着吗?你小子咋这不争气呢?这一记响亮的耳光加上一番连珠炮似的吼叫,让我对葛粉充满了无以复加的恨。葛粉是无辜的,亦如我的无辜。可恨是的贫穷和苦难。
挖葛根,是贫穷的村民唯一的生存出路。同时,给村人身体带来的是无尽地苦痛折磨。
由于长期在刺骨的冷水中浸泡、在寒风中劳作,一个冬季下来,父母的手掌、脸庞全部皴裂了,如干涸的稻田,企盼一场春雨。可他们始终都在冬季徘徊。寒冷和湿气也乘虚而入,如一条冰冷的蛇,钻进父母的身体,煨着取暖,带走父母仅存的一丝温热。它一蠕动,父母的关节就如火灼般疼痛。
门前的一棵橘树生了虫子,起先发现了一个洞,肥胖的虫子神泰安然地朝外伸展。父亲用蘸满了农药的棉花塞进去,甚至钉上铁钉。不久,又发现了另一个洞,父亲再堵,再塞。后来,发现这个树全部都是洞,这些虫子无孔不入,便也无从堵起。树心被虫子一步步啃噬,形容槁枯,摇摇欲坠。它顽强地屹立着,最终,没让自己倒下去。来年,依旧发芽、变绿,葱葱笼笼!它是一棵树,是树就得堂堂正正地站立,哪怕身上再多苦痛。
一种叫痨伤的病痛如橘树上的虫子一样悄悄钻进父亲的身体,在父亲羸弱的身子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咬噬父亲的筋骨。一到雨天,它们在父亲体内群魔乱舞。父亲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如一只离开水的鱼,痛苦地呻吟着。我身心颤栗,泪如泉涌。别呆在哪儿了,去卫生所里给你伯买几贴风湿膏,让他止止吧,母亲说。 贴得多了,疼痛也麻木了。父亲静了下来。村庄也静了下来。
阒寂的村庄,听到的是风的叹息,树的哀怨。
年关近了,母亲清早上街卖葛粉蛋,我也跟着去了。街上的年味浓了,琳琅满目的年货、五颜六色的装饰,让我目不暇接。我牵着母亲的衣角,躲在母亲的身后,如一只怯怯的小鸟,慌乱间闯入了农人的院落,滴溜 溜转动着眼珠,张望着一个陌生新奇的世界。大家都行色匆匆,满脸茫然。母亲提着篮子,沿着商铺挨家逐户登门拜访。老板,买两个葛粉吧,清热祛火,提神醒酒!母亲满脸堆笑。母亲的热情换来的是冷漠和鄙夷,他们对母亲的叫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偶有善良的老板会买一个、两个。5毛钱一个!咋这贵呢?4毛卖不卖?老板,我们整葛粉的人造孽啊,母亲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手中已经开始拣葛粉了。4毛就4毛吧,反正是咱自家的出产之物,母亲自我安慰。临近中午了,还剩了半篮子葛粉没卖。我的肚子早已发出抗议了。买根油条吃吧,我央求母亲。待一会儿给你买,再坚持一会儿,母亲使的是缓兵之计。走到百货商场附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小心打破了一瓶橘子罐头,小伙子怔了怔,扭头走掉了。母亲瞅瞅四周无人注意,红着脸,迅速将剩下的半瓶橘子罐头捡了起来。我坐在台阶上,对这半瓶罐头如获至宝,囫囵咽下。末了,才想起喂母亲一口。好甜!母亲咂着嘴说,流露出满脸的幸福。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罐头。半瓶罐头,珍藏的是两代人的疼痛、酸楚。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大雪封山,冰冻盈尺。北风紧了,呜呜地从村庄上的脊背上刮过。雪,把大地万物渲染成一个白色的世界,这个心怀叵测的家伙,来不及打声招呼,它就降临了。它的到来,让每一个脆弱的生命紧张、惶恐。父亲昨天搭车上县城卖葛粉蛋去了,说好了,今天回来。
这回你伯伯被隔在县城,又要遭罪了,母亲说。
夜里11点左右,父亲竟然回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这个风雪夜归人,从相隔60多公里的县城里走回来了。父亲打着电筒,拄着半截竹杖走了整整一天半夜。
母亲赶忙起床发了一盆红彤彤的炭火,熬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烤了半天,父亲僵硬的身体才有些许知觉,可鞋子怎么也解不开了,鞋子和冰块冻成了一个整体,鞋带的两端被冻成两个圆疙瘩,走起路来就像两个乒乓球样左右摇摆着。母亲找来剪刀,将鞋带剪断,父亲才把脚从鞋子里剥离出来。
姜汤,父亲没喝。父亲喝了两碗白酒。酒替父亲抵御了暂时的风寒,驱走了躯体短暂的疼痛。
自从发现酒可以止痛,父亲开始酗酒成瘾。父亲喝酒的样子很可怕,常常把自己喝到濒临死亡。高耸的颧骨上凸显着一对红肿的眼球,目光空洞,瞳孔被无限放大,仿佛要洞穿眼前的这个世界,尽管他始终未看通透。父亲形销骨立,一语不发,神情黯然,沉默得像块木头。如田地的庄稼,总是将苦痛隐匿于厚土。生活如酒,五味杂陈,父亲饮下的,唯有苦。酒帮父亲驱除身体的疼痛,却无法帮他驱除内心的疼痛。 暑假到了。我牵着家里的那头牯牛行走在孤寂的田野上。早晨的空气,湿漉漉的,透着薄凉。远山近水,全被一层雾岚罩住。几只不知名的鸟雀,跃上高高的枝头,声嘶力竭的鸣叫,将大地喊得一片苍凉。妹妹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放在简陋的桌子上,红彤彤的,发出耀眼的光芒,灼着父亲的眼睛,刺痛父亲的神经。父亲由于疾病和伤痛的困扰,去年冬季已经没有挖葛根了,整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如一个农民又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去年也是这个时节,父亲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将我送进了高中的校门,如今妹妹又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
正午的烈日,从院子中间那棵核桃树的枝叶间漏下来,投在地面上形成一块块光斑。我家的大黄狗横卧在院门口,哈哧哈哧吐着猩红的舌头。原本蓬勃热烈的花草们都无精打采,蜷缩着身体。父亲木木地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眼神呆滞,愁容满面。这注定是一个感伤的季节。
这个漫长的夏季,父亲在纠结和痛苦中度过,他醉了一次又一次。同样痛苦的还有妹妹,包括母亲和我。最终,妹妹辍学了,到了南方一家玩具厂上班。妹妹走的那天,父亲酩酊大醉,母亲以泪洗面。我和妹妹相拥而泣。
妹妹的辍学,让父亲背负一生的疼痛,让我背负一生的愧疚。每每回想妹妹打工离家出走的情景,我都心如油煎,百感交集。同时,也让我记住了冷和暖,爱和恨,也从此学会了承担和使命,感恩和敬畏。 日暮时分,我常常一个人跑到山岗上俯瞰村庄。四野岑寂,村庄的道路、房舍、草木……熟稔如我的掌纹。山坳间隆起的几座葛粉蛋状的坟冢,里面安息着我的亲人——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还有我未成年的姑姑。他们如葛粉一样,来自于泥土,又归于泥土。我静静地遥望着西沉的日头,它悬挂天际,光线由亮到弱,颜色由橘黄变得通红,然后一点点没落,消逝。残阳如血,刺痛了我的双眼。在我看来,它分明是一枚带血的葛粉蛋,一枚祖辈们用心血和生命孕育出的葛粉蛋。
泪水夺眶而出。 (市荟春杯文学大赛一等奖作品) |
上一篇:猎人的后代
下一篇:围猎旧事
- 06/28保康县历届主席团成员
- 04/282020紫荊花诗歌奖·“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
- 06/13姜雪琳
- 05/02文化保康建党百年大事记补
- 05/05李修平
- 07/01秦雨
- 05/12王明瑞
- 05/10高明英
- 07/10保康县第六届主席团成员
- 03/10“用爱征服,用心铭记: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
- 08/04保康诗词学会成立 山林支队再添轻骑
- 07/24避暑神农架
- 07/24在2021年度襄阳市作家协会年会暨“光华特杯..
- 05/26保康县作协开展“到人民中去”文学志愿服务..
- 05/25只留清气满乾坤
- 05/25只留清气满乾坤
- 05/01高昌英
- 05/01汪递强
- 05/01杨丽
- 05/01张咏
- 01/052022年保康作协工作总结
- 07/24在襄阳市作家协会 2021年会上的 致 辞
- 07/24文学盛会聚保康 山林支队获殊荣
- 05/26保康县作协开展“到人民中去”文学志愿服务..
- 04/20保康县作家协会2022工作会议召开
- 04/20抒写“红色黄堡,绿色乡村”笔会成功举办
- 12/27凝心聚力 为文学事业修路建桥 ——2021年保..
- 11/18保康县作家协会举行 学习六中全会精神、激..
- 11/01保康作协“助力惠游湖北·奉献文化情怀” ..
- 06/08李修平考察尧治河文学创作基地
保康作家网 bkzj.xysww.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保康县政府大院12号楼61327信箱
联系电话:13597488059 13908677897
投稿信箱:2052739087@qq.com 522456581@qq.com
法律顾问: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