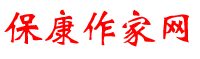远 去 的 童 年
时间:2019-05-05 点击: 次 发布者:褚金鑫 - 小 + 大
褚金鑫 一 肆虐的洪水过后,沙洲、滩涂上堆满了从上游漂下来的过木檩条、香菌桐、连根拨起的大树。村里的人倾巢而动,陈幺叔一群年青力壮的小伙们将粗大的木柴捡至岸边聚拢成堆,暴晒两日,扛回去,是上好的柴禾,村里人管这叫拣浪渣子柴。 我牵着妹妹,跟着成根、大柱子、小翠还有陈奶奶拎个竹筐拾些细小的木棒及一些遗弃的树皮。我们从不在意一天能拣多少,多数时候是为了能趟水或者打着拣浪渣子柴的幌子在河里洗澡整鱼。 直至河里空空如也,无柴可拾,成根就约我们一起拔掉巩固河堤的木桩、拦杆,当作战利品兴致冲冲的给扛回去。成根的父亲陈三叔当时是生产队的队长,一眼即识穿了我们的猫腻,问我们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成根将脸扭在一旁,嘟囔着说拣的。陈三叔两眼一瞪,你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这分明是抽的河桩,你当老子不晓得。说罢,将成根的耳朵狠狠拧了一圈又一圈,疼的成根泪花花直打转。我们耷拉着头,又将这些木桩、拦杆送回河里,陈三叔找人将它们恢复原状。 由于长期在水中浸泡,我那幼小的妹妹不幸患上了风湿腿。父亲带着她到几里开外的镇上去抓药,妹妹伏在父亲的背上,两只小手紧紧扳着父亲宽实的肩膀。崎崛的小道上,摇晃着父亲深一脚浅一脚的身影。回家后,妹妹还是嚷着腿疼,父亲就喂她吃一种木瓜丸的丸药。黑黑的如绿豆般大小,有时不慎掉在地上,如石子般脆响,园田边散落着一地的木瓜丸药瓶和包装盒。父亲黑着脸说,这都是你小子惹下的祸端。我勾着头,不吭声。后来感谢苍天眷顾,妹妹的风湿腿痊愈,压在我心头许久的罪孽感才如释重负。 二 成根说,他六叔要结新姑娘儿了(乡亲们管娶新娘子叫新姑娘儿,带个儿化音,听上去格外亲热、喜庆),我们一个个心花怒放。掰着指头掐算着,离陈六叔的婚期越来越近。陈六叔细高个儿,小伙子生得标志,一身好力气,近二百斤的木料往肩上一撂,健步如风,十几里的地儿从不歇口气。陈六叔也不上山搬木料了,头发用蜂花洗发水洗了一遍又一遍,拿个小镜子对着梳个四六分,拿瓶花露水对着胳肢窝喷,桂花香型,香得很哩。 盼望着,盼望着,陈六叔的婚礼如期举行,村子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新娘子是我们后山上的姑娘,父亲们清早匆忙喝碗面条,赶到后山上抬嫁奁。正午时分,阳光穿过窗棂,洒一屋的绯红。新娘子到了,一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浩浩荡荡的队伍让我们看傻了眼,红烫烫的嫁奁闪着耀眼的光芒。新娘子清丽可人,通身红艳艳的,头上戴朵红花,由成根的一些姑妈们搀扶着,一步一颦。锣鼓手两眼放直,双手加重了力度,加快了节奏,恨不得把锣砸穿,把鼓敲破,仿佛是他们娶新娘似的。满嘴黄牙的喇叭师傅双目圆睁,腮帮子鼓得像气球,叫人不敢相信那绵远悠扬的曲调是从他们口中出来的。他们吹了一曲又一曲,吹古典的《百鸟朝凤》,也吹流行的《纤夫的爱》。知客先生开始主持婚礼仪式,拿个红纸条照着念。他那如洪钟的般的声音从我们耳边拂过,混杂在呛人的火药味中,一溜烟袅袅飞上了青天。我们眼睛鼓得如铜铃,紧紧地把方桌上的花花绿绿的糖果盯住,一对红红的蜡烛兀自簌簌滚下嫣红的泪珠。待知客先生宣布新郎新娘入洞房、抢果盘时,我们一群小孩一哄而上,如风卷残云般,连掉在地上的也一颗不剩。趁喇叭师傅吃饭的空儿,成根壮着胆子,将喇叭悄悄胡乱吹了一通,可惜没吹响。 不到一个月,陈六叔死了。陈六叔是喝农药死的。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陈六叔和新媳妇不合,有的说陈奶奶和新媳妇不合,反正都与新媳妇有关。陈六叔死后,新媳妇也走了,走时不停地抹着泪,还带走了红烫烫的嫁奁。转瞬之间,陈六叔由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变成了一堆黄土。成根说他六叔的坟上供着不少桔子、苹果、馒头之类的供品,约了我一起去偷吃。我胆小,说不敢去,怕偷了陈六叔找着头痛。成根说,不用我动手,只用打伴即可,他去偷,是他六叔,不会让他头痛的。一个黄昏,我就跟着去了,五颜六色的花圈在风中猎猎作响。我隔了几米远的距离,立在那里观望。成根独自一人摸到坟前,一会儿就用塑料袋装了满满一袋。他拿一个苹果递给我吃,我心中还是有一丝惧怕,没敢吃。成根吃得津津有味。后来,果真如成根所说,到底是他六叔,也没找着他头痛。 三 小时候经常头痛,一痛,头就嗡嗡作响,仿佛要爆炸似的。我便哎哟哎哟叫开了,父母都吓住了,赶快去喊二婶立水柱子。二婶取一根筷子,用手扶着端端正正地立在灶台上,顺势蘸点清水,口中念念有词:“是不是娃儿的奶奶亲热他了,若是的,就请你站住”。手一松,筷子轰然倒下。二婶又接着说“是不是娃儿的外婆亲热他了,若是的,请你站住”。刚一放手,筷子又倒掉了。如此几番,只至二婶提及了二爷,筷子立马站住了。立了一阵,二婶说,二爷你走吧,赶明儿叫娃儿给你捎些钱过去。话音刚落,筷子就倒下了。说来也怪,刚才还头痛欲裂的,立竿见影,头也不痛了。有时二婶说了送钱赔罪之类的,筷子还是立着,二婶就用菜刀作势将筷子砍倒。然后我们就提了火纸、鞭炮到二爷的坟前磕头烧纸。有时明明头没痛,我也捂着头喊叫疼,只是为了目睹那神奇的筷子。待筷子立住了,父亲问我,还疼吗?我嘟哝一句,好了。 四 放暑假了,大柱子领着我们上他家的阁楼看燕子喂食。 大柱子家人多口阔,住两间逼仄的土屋,在后山的山顶隐隐看去像个小小的鸡笼。一间作厨房兼客厅,长年烟熏火燎,满屋子不见丁点儿白,黑黢黢的的墙壁上挂满了鱼网、土铳渔猎工具。还吊着一些动物的皮张,麂子皮、野免皮、松鼠皮,还有黄鼠狼皮,长长的尾巴都拖到地面上了。这些皮张内脏用谷壳填充,活灵活现。另一间作了卧室,对着支两张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大床是大柱子的爹妈睡的,小床是他两个妹妹睡的。两床中间留一狭窄过道,容得下一个人进出,若是遇个胖子则要侧了身子方能进去。过道尽头是一盘棍棍梯,踩着棍棍梯上去是阁楼,大柱子和他奶奶就住在楼上。刚开始上棍棍梯还有点害怕,颤颤悠悠的,走的多了,也就不怕了。对于大柱子住的阁楼,我们既好奇又羡慕。站在楼上,打开窗户,可以看见河对岸化工厂高耸的烟囱,如立在眼前一般。还可看见屋檐下燕子喂食的情景,我们目不转晴地盯着大燕子觅了食物喂给那些张着嫩黄小口嗷嗷待哺的小燕子,看得真真切切。 大柱子的老爹中等个儿,满脸横肉,胡子拉碴,头发直立,脾气暴躁,终日阴郁着一张黯黑的脸,仿佛谁亏欠他似的。他爱好上山打猎(我们那里管叫打铳),下河摸鱼,用大柱子母亲的话说叫不务正业,还有一种说法叫“打鱼摸虾,误了庄稼”。夏天的雨水多,一遇到下雨天,就不用下地劳作了。清早,大柱子老爹喊来一干人在屋里玩牌,玩“升级”、“滚轱辘”、“5、10、K”。不来钱,也能守在那里玩一整天,只是狠命地拿着大柱子家劣质的烟抽,七零八落地散落一地的烟蒂。到了午饭时间,大柱子老爹拉下一张黑脸,眼睛鼓得像牛卵子(大柱子娘说的),眉头一皱,两道浓黑的眉毛拢在一起,冲大柱子老娘嚷道“几点了,咋还不搞饭吃”。大柱子老娘拿眼晴剜他一眼,嘴里嗫嚅着,搬个小凳出门掐四季豆。大柱子老爹顺手抓了一张小王,哈哈打得像倒核桃似的。这干人在大柱子家里吃了午饭,继续玩牌、抽烟、打哈哈,一直持续到天黑,拍拍屁股,走人。 大柱子的奶奶爱抽旱烟,搬个木凳,坐在门前的白杨树下吧嗒吧嗒的能抽一个下午。一个硕长的水烟袋,吸起来咕噜咕噜作响。脸上的皱纹随着嘴巴的龠动拉开又收紧,隔一会儿咳嗽几声,舌头再搅动几下,呶呶嘴如运气般猛地啐一口黄痰,啪的一声,落得老远。抽了一阵子,她把烟锅放在石板上一番抡敲,装了烟丝,继续抽,继续吐。我们一般不靠近她,从她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旱烟味儿呛得让人实在难以忍受。到了夏天,大柱子奶奶在阁楼上尽顾敞着怀,胸前犹如挂着两条干瘪的丝瓜,见我们上去了,也不避嫌。 五 大狗子家是我们村最富裕的,可他为富不仁,净使一些阴招,使唤他的兄弟二狗子和我父亲吵架,霸占我们的老屋地基。我心里恨透他了。瞅住机会,我想狠狠报复一下他。 他家的菜园就在我家门前,由于离水井近,大狗子的老婆酆大娘精心侍弄,菜园子拾掇得有模有样。最打人眼球的要数南瓜了,拳头大小,绿映映的,水灵灵的,南瓜藤上开着黄花,花蓬蓬的。眼瞅着无人,我约了成根、大柱子,用小刀把一个拳头大的南瓜切一个小口,将粪便从切口灌进去,然后将切掉的小块原封不动地封好,看上去与别的南瓜毫无二致。 待过了几日,南瓜长得有舀水的葫芦瓢大小了,酆大娘兴冲冲地摘了回家。用刀剁开,一股浅黄恶臭的秽物如晃了瓶子的啤酒般喷涌而出,溅了她一满脸,搞的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过了好一阵才明白过来。便跑到稻场边上双手叉腰扯开嗓子骂:谁家的小孩没爹没娘没屁眼,干出这等的龌龊事来,烂心烂肝烂肺,活不过腊月三十。酆大娘极尽所能、搜肠刮肚的拣了最恶毒的词语来骂,有些稀奇古怪的,我竟从未听说过。声音大得犹如村子里那架挂在成根屋后白杨树上的高音喇叭,大有余音绕梁之势。我、成根、大柱子躲在我家厕所里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平日里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也仿佛没有了臭气。酆大娘站在稻场上骂得歇斯底里、声嘶力竭,跺跺脚进屋了。 六 六月的天,娃娃的脸。雨过天晴,清新的空气里洋溢着丝丝的香甜,直往鼻孔里钻,纵了鼻子嗅一嗅,香气沁入心脾、深入骨髓。后山上的地攀果(藤蔓植物,匍匐于地下,果肉状如草莓,细腻香甜)红了。我们赤着脚,忙不迭地跑到后坡里翻地攀果。我们如搜寻猎物般,东翻西寻,凭着敏锐的嗅觉,大大小小的果子被我们尽收囊中。 正当我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突然从天空里传来一阵凄厉的喊叫。仰头一看,湛蓝的天空中,一只老鹰扇着大翅膀俯冲直下,锋利的爪子牢牢的抓住一只怆惶逃命的飞鸟。飞鸟拍打着翅膀,做殊死挣扎,最终都只是徒劳,它扑腾了两下,息了锐鸣,垂下了头颅,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草草结束了。惊心动魂的厮杀离我们仅咫尺之遥,我们都看呆了。大柱子捡起一块石头往老鹰扔去,我们也尾随着冲老鹰扔石块。老鹰最终弃了飞鸟,盘旋在空中,久久不愿离去。成根飞奔到二婶红薯地里拣起了这只飞鸟,用手摸摸,身体还是温热的。原来这飞鸟是只鸽子,一只从南方飞过来的信鸽。腿部系有一只塑料小环,记载着这只鸽子的身份编码及来历。一路上,我在猜想,这只鸽子肯定是和同伴失散了,迷了路,飞越一路千山万水,没料到会在这小山沟里丢了卿卿性命。我们把拾到的这只鸽子送给了村里的周二爷,周二爷给煮着吃了,说香得很呐。 七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漫山遍野的焦黄被簇簇新绿替代。“促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桃花红、杏花白,黄莺鸣叫,燕子飞来,蛰伏了一冬的虫子也从轰隆隆的春雷中惊醒,伸伸懒腰,舒合舒合筋骨,从地里冒出来,从石缝里钻出来,张望着新奇的世界,在旷寂的原野上欢快的爬行,嬉戏。 父亲说,后山的蜈蚣又出来了。 春雨过后的黄昏,父亲扛把镢头,拧个罐头瓶子,带个自制的摄子,到后山上逮蜈蚣。我趿着一双破鞋,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身后看稀奇。蜈蚣为节肢动物,属“五毒”之首,父亲叮嘱我千万不要沾惹它。蜈蚣天性畏光,昼伏夜出,喜欢在阴暗、温暖、避雨、空气流通的地方生活,主要生活在多石少土的低山地带,多潜伏在砖石缝隙、墙脚边和成堆的树叶、杂草、腐木阴暗角落里,后山的摞荒地里是它们的最佳栖息场所。父亲用撅头撬开一块又一块石头,冷不丁就从里面钻出一条蜈蚣出来,张开“千足”一浪浪向前爬。父亲把它踩在脚下,用镊子夹住,丢进瓶子。起先它还紧贴着瓶壁试图往上爬,无奈瓶壁太光滑,哧溜又掉下去。我们跑遍一个个山坳,不停的翻着石头,待到天麻黑时,蜈蚣就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一罐头瓶子。 回到家里,就着昏黄的灯光,父亲用摄子将蜈蚣取出,用左手大拇指跟食指捏住它的颈部,它的两根毒螯自然张开,尾部顺势缠在父亲的四指上。父亲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把它两根张开的毒螯掐掉。然后取了两头削尖的竹篾片,一端插入蜈蚣腭下,另一端插入尾部,借竹片的弹力将蜈蚣伸直,一排一排摆得密密麻麻的,有点像过年燃放的鞭炮。将串好的蜈蚣置阳光下晒干,就可拿到街上卖了。大的三毛,小的两毛、一毛,也能换回一堆花花绿绿的零钞。钱不多,却能给我们贫寒的家庭带来一丝春意。 家乡有个传说,说蜈蚣长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成精。成精之后,它一般躲在坟墓里或者粗大的松树里。为了防止它祸害生灵,雷公老爷会收拾它。后山上李老七的坟墓在一个夏天被一声炸雷给劈开了,石头滚得七零八落,里面躺着一条尺把长的蜈蚣,全身殷红,这些都是宋二爷讲给我听的,至于那条蜈蚣,我没见过。但我亲眼见到李氏后人又重新把李老七的坟墓修葺一新,用水泥浆浇了一遍又一遍。二叔山上有一棵几人合抱的古松被雷给劈开了,周二爷说这是上好的木料,用作房屋大门再好不过,可以镇妖祛邪。二叔便找了几个年轻力壮小伙子给扛了回来,一直放到现在,二叔家新盖了楼房,这两段被雷劈开的木料没派上用场。 八 村子里的春秋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岁一枯荣,淡然而又漫不经心。大柱子、成根留在了村子里,结婚、生子、变老;沮河涨水的时候,满河里尽是黑压压的浪渣子柴;大柱子的老爹挎着一只土铳四下里打野免、打斑鸠,只是头发白了一圈;陈六叔的坟莹上长出了参天大树;水井边的南瓜水灵灵的;后山上的地攀果红了,蜈蚣肆无忌惮的满山跑。红的花、绿的草、黄得土,虫鸣、鸟叫,流泉、飞瀑,阳光、雨露,与村庄朝夕相伴、亘古不变。 这么多年,我一路跌跌撞撞,只是为了逃离那贫瘠的故土。残酷的现实令我遍体鳞伤、心力疲惫。经年以后,召唤我在某个季节回乡的,仍是童年的时光片羽。 |
上一篇:亲爱的汤老师,您还好吗?
下一篇:二姐
- 06/28保康县历届主席团成员
- 04/282020紫荊花诗歌奖·“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
- 06/13姜雪琳
- 05/02文化保康建党百年大事记补
- 05/05李修平
- 07/01秦雨
- 05/12王明瑞
- 05/10高明英
- 07/10保康县第六届主席团成员
- 03/10“用爱征服,用心铭记: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
- 05/01王承鼎
- 05/01张蕾
- 05/01田雪梅
- 05/23局长的手机铃声换了
- 04/20抒写“红色黄堡,绿色乡村”笔会成功举办
- 05/20贺《荆山文墨》发刊
- 12/27与伟大时代共呼吸||李修平
- 05/20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哭
- 05/20黄青玲
- 05/20保康迈吧河户外运动——攀树
- 01/052022年保康作协工作总结
- 07/24在襄阳市作家协会 2021年会上的 致 辞
- 07/24文学盛会聚保康 山林支队获殊荣
- 05/26保康县作协开展“到人民中去”文学志愿服务..
- 04/20保康县作家协会2022工作会议召开
- 04/20抒写“红色黄堡,绿色乡村”笔会成功举办
- 12/27凝心聚力 为文学事业修路建桥 ——2021年保..
- 11/18保康县作家协会举行 学习六中全会精神、激..
- 11/01保康作协“助力惠游湖北·奉献文化情怀” ..
- 06/08李修平考察尧治河文学创作基地
保康作家网 bkzj.xysww.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保康县政府大院12号楼61327信箱
联系电话:13597488059 13908677897
投稿信箱:2052739087@qq.com 522456581@qq.com
法律顾问: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