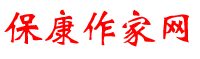杨龙声
因为工作关系,北京《人民文摘》的王编辑给我发来短信,称我为杨老师。作为陌生人,这样称呼我完全是出于礼节,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真的当过老师,而且是整整17年,不过是那种地位、待遇各方面都不能与公办教师同日而语的民办老师,简称“民师”。不知不觉间,离开讲台已经十来个年头了,人也到了知天命之年。除了部分当年的学生,已经很少有人再叫我“老师”了。忙碌之中,寂寥之时,偶尔被人这样称谓,反倒觉得很惬意。 当民办教师,教书十几年,耗费了短暂人生的一大段时光,现在想来并不觉得遗憾。想当年,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领着少得可怜的薪水,成天和孩子和课本和黑板打交道,教语文代数学办墙报演节目搞春游,虽然被很多人瞧不起,但日子过得其实很充实。现在每每听到那些已经有出息混得比我强的学生向来客向领导介绍说我是他们的老师时,还是很高兴很自豪的。单位里有不少人都是当年的学生,现在成了同事成了我的上级,关系处得蛮不错。工作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生活上彼此尊重相互照应,说话做事挺随和。酒桌上海阔天空,闲暇时鸡零狗碎,兴致高时他们在我这个“先生”面前的措辞偶尔有点“出格”,我也并不怎么在乎。那些已经走出大山在外工作、谋生的学生们经常通过QQ、电话嘘寒问暖,回乡后总会找上门来,递支烟聊聊天讲讲山外的见闻。编织成这么一张特殊的人际关系网,我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来之不易,我相当珍惜。想当年一年只能挣一两千块钱,虽说紧紧巴巴日子也还是挺过来了。现在一年三万多,照样是穷人照样经常捉襟见肘照样欠账。所以我总结,没有钱不能生活,但钱不是生活的全部。只要日子过得充实,从事什么工作有多少收入似乎都并不那么重要。每当在办公室郁闷纠结的时候,或者是芝麻绿豆的杂事赶到一块儿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会经常想起教书的岁月。虽然教书也忙,晚上备课改作业清早起来带操上自习,但比较单纯,有一定的规律性。如今在办公室婆婆妈妈事情多,稍有疏忽就会出差错,纵使领导不批评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闲忙也没个谱,闲的时候可以成天静坐看看书翻翻报纸接接电话,忙的时候连夜赶写材料布置会场跑进跑出迎来送往搞得焦头烂额。老师不好当,事事处处都要为人师表,不迟到不早退,一言一行都得检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切都成了习惯,一切都循规蹈矩。到村里上班后,看到有些人随随便便大大咧咧,作风飘浮语言粗鲁做事马虎得过且过,总是看不惯,免不了摇头叹息,有时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背地里或在各种会议上大发感慨,惹得人家不高兴。教书十几年,有得也有失。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也落下了不少后遗症。说小的,中午总爱小睡一会儿,免得下午呵欠连天。到村里上班后,经常是中午开会做事加班加点,到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说大的,天天接待上级领导,天天与相关部门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对上不甚了解官场的潜规则,对内部个别点头哈腰阿谀奉迎的人总是看不惯,有时还在知己面前或通过网络发点牢骚。无端地得罪人,给人以另类、老古董、狗咬耗子的感觉。曾经当过老师,而且时间还不短,清贫而不寂寞,说不上辉煌但也不算平庸。不后悔,有时反而还觉得自豪。民办老师,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群,相信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被历史遗忘。要不,刘醒龙的小说《天行者》怎么会获得茅盾文学奖呢?看到一群在井边捉青蛙快乐玩耍的学生,我又想起了当年做民办老师时那一个个打工挣钱的暑假。我们民办老师工作量大教学成绩跟那些正牌老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工资却只有他们的一个零头,同工不同酬。被辞退的前两年我的月工资才好不容易闯过了200元大关,作为一家之主,其艰辛与难堪可想而知。那时候年轻,体格也不错,轻重的活计都不在乎,修路、烧炭、打矿粉,还到矿山上做过小工。虽然热虽然累但干得有劲头,一个暑假能挣回差不多半年的工资。每当假期结束回家见到老婆孩子的时候,我总能从他们欣喜的眼神中得到满足。凭一身力气换来儿女的学费和妻子的汗衫,我在充分展示着自己三寸不乱之舌之外的价值,一次次获得学生家长们“能文能武”的赞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暑假,我们几个同事兼知己找到刚当矿长不久的孙开林,去尧治河承包了一个小工程,降低一段矿山公路的路面。大部分是土方,不用放炮,用十字镐挖用钢钎撬,然后用板车推走倒进前面拐弯处的深沟里,工具都是从学生家里借来的。毕竟不是经常干重活,开始几天个个手打泡,饭量也变大了,向来不爱吃大米干饭的我也能一顿来上几大碗。晚上躺下后那几位还在聊着家长里短,我就呼呼睡着了。好在管工地的黄大哥是学生家长,总是时不时过来递支烟,招呼我们坐下歇一歇聊聊天。有一次,我一走神儿没控制住把借来的板车推下了大沟摔得面目全非,害得一刚熟识的当地民工花了半天时间才修好。完工那天,孙矿长让出纳当场把钱递给我们,还陪我们喝得醉醺醺的。凭体力也凭关系,我们捞到了“第一桶金”,每人分得一沓大团结,美滋滋的回家报喜。烧炭的活我教书以前就干过,无非是砍柴扛柴装窑出窑。毛力气倒是有一把,但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我不会,装窑出窑时都打下手。那年刚放暑假我就跟几个弟兄骑着自行车到神农架一个叫萝卜峪的地方去烧炭。包工头是孩子他舅,对我挺照顾。大热天的,吃过午饭还得睡上一觉,快三点了我一催再催他才起床慢悠悠地拿着斧头上坡。干的时间不长,刚砍倒几棵树,他又跑过来给我点烟,说热得汗直冒干脆早点收工。不习惯的是一下子住进用竹竿、薄膜撑起来的工棚,晴天像蒸笼,下雨像敲鼓。床也是用木头和竹棍现编的,麻烦的是入睡前眼镜没地儿放,只好递给睡在一起的幺弟,让他塞进头顶的石缝里,第二天早上又让他递过来。窑建在半山腰,根本没有水,要烧“干窑”,出窑时只好把红彤彤的银炭埋进土灰里。老师傅用长木棍从窑里把炭拨出来,我得抓紧摆放整齐,一层层盖上土灰。火候到了该出窑时就得出窑,太阳再厉害也得抢着干,不然炭就化了。头顶烈日烤炭火,出汗太多就歪着头用衣袖随便一擦。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就摘下来直接用手指抹一抹,或者放在地上让风吹一吹。旁边放着一壶从山脚下提上来的泉水,渴了抓一大把白糖放进罐头瓶子里,倒进凉水摇一摇就一饮而尽,越出汗越要喝水。那个暑假的“高温作业”让我落下个毛病,小便频繁而疼痛,后来问了医生才知道可能是前列腺出了点问题。又一个暑假,外面来人在村里的矿山上打探矿隧道。那时公路还没通,各种机械都是靠人工从十几里外抬上来的。力气活是我的强项,白天跟着一大群人吆五喝六抬机械,晚上还要在月光下指导排练去镇上参加七一晚会的节目,算是劳逸结合。后来我又缠着从县城来的何老板,把开挖隧道洞口的活儿承包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了一回小包工头,带着几个小兄弟一起干。完工后,除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工资,还象征性地拿了点儿提成。好像是澳门回归那一年吧,我去镇上的矿粉厂挣钱。三班倒磨矿粉,一干就是8个小时。在灰蒙蒙的车间里用袋子装矿粉码堆,又脏又重,弟兄们好歹不让我干,我每次都负责往破碎机里上矿。遇到大块的要捶碎,三个人比着干,斗子满了可以歇一会儿。更深夜静,打着赤膊垫块纸壳子倒在矿堆上仰望星空,静听哐当哐当的机器声和稻田里的蛙鸣,强打精神等待天明。有时赶上正午下班,就迫不及待地抱着衣服去附近的温泉洗澡。配电室的小胖子发现我是个“旱鸭子”只敢在边上扑腾,冷不丁将我推进深潭里,估计呛得差不多了才把我拽起来,善意地拿我开心。上大夜班白天就只有睡觉,遇上突击发矿粉还能装车挣现钱。几个人光着肚皮赤着脚把120斤重的矿粉袋子抱上车码整齐,你来我往,看谁跑得快,一个个白乎乎的,那场面记忆犹新。大半个月没回家,休班时我给儿子写便条,要他好好写作业;还绞尽脑汁给刚失恋的女同事写了封长长的信,请矿车捎回去,那时村里还没通电话。那个暑假,干的活挺新鲜,挣的钱也最多。家门口的矿山热闹起来之后,每个暑假我都在那儿干。也下矿井出过矿,活并不算重,关键是不具备井下作业的心里素质,没干多久便改行当了建筑工地的小工。挑砂浆,搬水泥砖,这些活对我来说都很轻松。那天下午在新建的工棚上盖瓦,踩断了椽子跌到地上,把矿长吓得一声大叫。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又接着干,后来才发现腰部还是有暗伤。教书十几年,经历好多个暑假,干过好多的活,不仅仅是挣到了钱,也体验了无穷的快乐与伤感,品尝了诸多的酸甜苦辣。人生就像电视剧,就该有曲折起伏,没有绝对的一帆风顺。要是没有这些暑假打工的历练,若干年后我就只能索然无味地告诉孙子,爷爷年轻时曾经当过老师,后来又如何如何,那多没意思啊! |